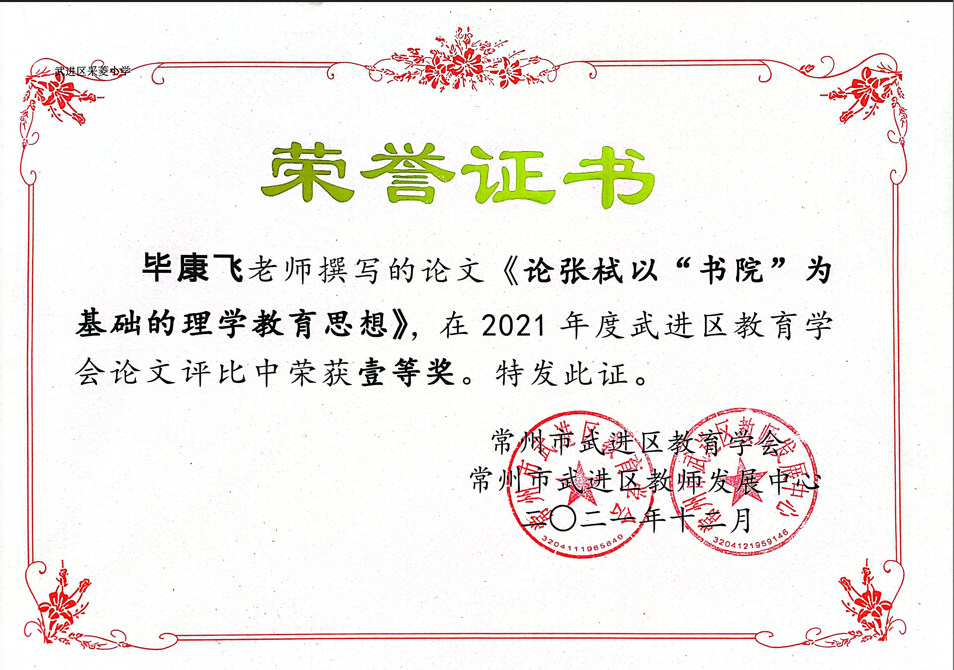
论张栻以“书院”为基础的理学教育思想
摘要:众所周知,张栻作为南宋时期理学家,也是最早提出以书院思想来传播理学的人。张栻以书院为基础的理学教育思想不仅充分展现出了南宋理学教育的风气,也展现出了自己的独特之处,那便是将道德教育提升到了本位,将儒家思想彰显得淋漓尽致,同时也为儒家思想内容增添了新的元素。本文将就张栻以“书院”为基础的理学教育思想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究。
关键词:书院思想 理学教育思想 张栻
引言
继春秋战国之后,南宋乾淳时期是又一个学派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各个学派互相争鸣、百花齐放的现象再次出现。其中,张栻便是诸多优秀学派代表之一,其代表的是湖湘学派,张栻更是湖湘学派的奠基人。张栻在理学以及书院发展中所做出的贡献丝毫不比吕祖谦、朱熹等人逊色,后世更是将张栻与吕祖谦和朱熹并称为“东南三贤”。对于张栻而言,对他产生最大影响的应该是书院教育,这也是他以书院教育为基础来传播理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张栻的书院教育思想全面展现出了南宋理学教育的学风,但也有着自己的学风特色,即以“性”为本体的德教思想,重视实践,形成了兼容并蓄的学术风格,张栻以书院为基础的理学教育思想在现代教育教学工作中依然有着自己的独特价值,为实际教育教学改革工作提供了重要借鉴意义。
一、思想核心:以“性”为本体的德教思想
我们都知道,儒家育人思想向来以德教为重,比起学业上的传授,儒家更看重人品道德的培养。张栻便是儒家育人思想的代表人物,在保留恩师胡宏“性本论”的精髓之上又有着自己的思想主张。张栻以“性本善”为核心,构建起了以道德伦理为本位的道德教育学说,在该学说中,张栻并未认可其恩师的“性本无善恶之分”的说法,而是汲取了孟子“性善说”的思想,认为性是至纯至善的,而善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质。张栻的《孟子说》中有这样一段话:“所谓善者,盖以其仁、义、礼、智之所存,由是而发,无人欲之私乱之,则无非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矣。”从张栻这一段阐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栻心目当中的先天善性和封建伦理道德原则有着高度一致性,其都是将仁、义、礼、智作为了具体内容,并且张栻心中的“性”有着至尊至贵的本体高度。
张栻认同的人性本善,是出于对天命之性的认知,而不是出于对现实的认知。张栻已经认识到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到底如何并不完全依赖于先天性格,后天的教育和环境对性影响要更大一些,而且人只有接受良好的教育,具备了排除外物影响和干扰的能力,才能够有空间发挥自己的善良本性。而这也证明了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对于培养人的道德品质,引导人向善有着很大的积极作用。
在张栻的一生当中,他一直都将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从岳麓书院的堂训、学则以及学规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张栻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岳麓书院以塑造圣贤人格和陶冶道德风尚为目标,从岳麓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更是一直坚守着圣贤风骨,才有了“潭州之陷,岳麓三舍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尤多”的记载。岳麓诸生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与张栻的教育理念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正是有了张栻之引领,其后学才可以伟岸人格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得立于世,成为天下士子的楷模。
二、重视实践,重新彰显儒家思想的务实品格
当时儒家伦理纲常是被奠定在终极存在哲学本体之上的,有一大批学者们都将关注点集中在了空谈心性和哲理辨析上面,导致儒家之前一直都非常重视的道德践履受到忽视,务实品格也不再被提起。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张栻始终保持着理性认知,重视实践,极力反对空谈心性、不务实际的学风,坚持认为学者只有务实,才可真正有所收获。张栻将务实定义成为于践履中求知,要在实践当中去探究真知和道理。张栻主张学者需要在待人接物、言谈举止之间去体察奥妙,既要在实践中去获得经验和认知,而不是空谈理想,整日处于虚诞空无当中,还自认为自己掌握的是人家真理。张栻在教学过程中会非常强调务实,而且他将修身齐家、事君泽民全都纳入到了学子们需要实践的内容体系当中来。与张栻并称为“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是这样评价张栻的:“张荆州(张栻)教人以圣贤语言见之行事,因行事复求圣贤之言语”。
深入分析张栻主张务实的理论基础,其应该是“道器说”。张栻虽然和朱熹、陆九渊一样也将世界区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但是,张栻认为形而上和形而下并不是断层的,而且二者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形而上的道是存在于形而下的具体器皿当中的,也就是我们大众所理解的物不离道和道不离物的关系。道虽然不是器,可是现实社会中的治世之道却是要借助各种物质载体,诸如钟鼎、钟鼓、玉帛等来体现,因此,道需要以器物作为载体,张栻坚持的是从形而下的器物当中去探索形而上的宇宙本体,是一种具象到抽象的升华,可是,张栻所言的道绝不是缥缈的存在,而是切切实实存在于四季变幻、渴饮饥食当中的,而且如果没有这些物质载体,那么道也便不会存在了。
三、以“传道济民”为宗旨,彰显儒家价值观
儒家传统价值观中,内圣外王是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儒家思想不仅仅关注学子们个人道德修养的引导和提升,也给予了治国、平天下这种外王事功高度的重视。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普遍将教育的目的定义为发明圣道、接续道统,培养圣贤人格,对穷理灭欲表示出高度赞同,这样的思想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便慢慢导致了外王层面日益断裂和萎缩的局面。张栻作为南宋时期的理学家,其价值观念自然会受到朱熹和陆九渊所推崇的道学思想的影响,但张栻也因为受到自身成长环境以及所接受的湖湘学派理念的影响,并未将心性义理的内圣之质和经世致用的外王事功割裂对立开来,而是将二者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其从张栻为岳麓书院撰写学记时提出的“传道济民”的办学宗旨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张栻的观念当中,学校应该承担起传道济民的责任,传承圣人之道,引导学子承担起儒学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大业,并运用所学知识为民众造福,把自己的所学用于帮助世人当中来,要让自己成长为经世济国的人才。学校绝不是为世人提供群居闲谈的地方,更不是为生徒传授文辞工巧以猎取功名利禄的场所。
深入分析张栻的传斯道济斯民的思想以及对学校提出的办学要求,其和传统儒家内圣外王之学有着高度一致性,传道济民的思想既包含了心性义理之学的内容,又兼顾了经世事功的内涵,而且还包含了当时理学主要流派代表人物朱熹和陆九渊注重心性修养的理学特征,此外还兼具了叶适、陈亮的外王事功的特色。
四、容百家之长,不拘泥一隅
自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学派不断涌现于世,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家族流派争芳斗艳,各学派思想也各有千秋。在这种百花齐放的盛况下,学派间出现了“排他”现象,为了稳固各自学派的地位,各学者奉行“排斥异端”学说,学者们都坚持只有自己的思想才是正确的,只有自己的主张才能匡扶社稷、传道济民。这种排他性愈演愈烈,到了张栻所处时代尤为严重。永嘉学派叶适和永康学派陈亮主张的“功利”学说和朱熹提出的“心性”论相对,而陆九渊倡导的“心学”又与各学说相抗衡,各学派间相互竞争、相互贬低,严重阻碍了学说的交流与发展。
张栻却没有拘泥一隅,而是容百家之所长,他不但继承了自家学说,还吸收了众多理学家的正确思想与主张,与同辈学者进行交流会谈,湖湘学派也因此有了进一步的开拓,变得更加成熟。就连张栻的门生也深受其影响,他们基本传承了张栻的教育思想,不但强调天理具有客观约束性,而且突出了人的内心具有主宰作用;既重义轻利, 强调用“义”治理天下 ,又留心经济之学。他们摒弃门第之见,各从心仪之学说,具有不执一端、兼收并蓄的特征,为岳麓书院的建立扩大奠定了基础。
张栻博采众长,不囿于成见,经世致用的这种精神体现了他博大的胸襟,对湖湘学派的形成、发展和理学的丰富、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得湖湘学派“在当时为最盛”。
结束语:
综上所述,张栻以书院为基础的理学教育思想是南宋时期思想教育发展的代表性产物,该理学教育思想不仅代表着对南宋主流理学教育学风的继承和发扬,又呈现出了与正宗理学不同的一面,充分展现出了自己的特点。张栻以书院为基础的理学教学思想在当前教育教学中利用应用和指导价值依然不容小觑,因此,加强对该理学教育思想的研究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 贾淋婕. 论两宋书院的流变及书院与理学的关系 ——以两宋湖南地区书院为例[J]. 文博, 2020, (001):73-77.
[2] 黄麟. 宋代理学家的吟咏书院诗——以张栻和魏了翁为中心[J]. 青年文学家, 2019(9):63-63.
[3] 刘师健. 论张栻的文学观与其文学风貌[J]. 湘南学院学报, 2019(4):49-52.
[4]谢桃坊. 论学辩难 穷理致知——试析张栻与朱熹关于理学观念的讨论[J]. 天府新论, 2019(6).